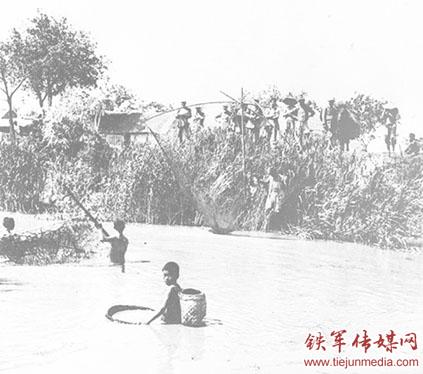
阿英,原名錢杏邨,安徽蕪湖人。我國現(xiàn)代著名的文學家、戲劇家、文學史家和藏書家。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,1927年冬與蔣光慈等組織“太陽社”,編輯出版《太陽月刊》《海風周報》等革命刊物。1930年參加“左聯(lián)”,并任“左聯(lián)”常委、文總常委,他冒著風險,在安徽蕪湖、上海等地積極開展革命活動。
1941年12月8日,太平洋戰(zhàn)爭爆發(fā),阿英根據(jù)中共地下組織的秘密通知,毅然攜帶四個孩子,舉家從上海前往蘇北抗日根據(jù)地。
阿英的女兒、新中國成立后擔任蘇州市宣傳文化部門領(lǐng)導工作的錢瓔大姐,對當年的情景,依然記憶清晰。筆者將她親歷親聞父親的許多鮮為人知的往事,作文以記之。
被葉飛盛情挽留在一旅工作
1941年歲末,隨阿英到蘇北抗日根據(jù)地的家人,有女兒錢瓔、長子錢毅、次子小惠和三子厚祥。錢瓔最大,18歲;最小的厚祥只有12歲。一家五口分兩次從上海十六鋪碼頭乘船,經(jīng)過一晝夜的行駛,到達蘇北張黃港上岸會合,又冒著黑夜經(jīng)過一番奔波,到達了蘇中三分區(qū)新四軍一師一旅的駐地。
早就聽說過阿英大名的新四軍一師一旅旅長葉飛,對于這位大文人的到來非常高興。葉飛熱情地安排了接待活動,他將一旅的戰(zhàn)斗、生活情況,向阿英一一作了介紹。
初到根據(jù)地,阿英感到這里的一切與上海有天壤之別,而這些都是可用以寫作的生動感人素材。令阿英出乎意料的是,葉飛提出希望阿英能留下一段時間,幫助指導一旅的文化工作。而阿英覺得剛到蘇北根據(jù)地,也極需要了解、熟悉和感受這里的戰(zhàn)斗氣息,所以就愉快地接受了葉旅長的邀請。對于阿英樂意留在一旅工作的表示,葉飛高興得樂不可支。于是,他提出請阿英到服務團幫助開展文藝工作。阿英當即表示盡快到服務團參加活動,并安排錢瓔和錢毅到服務團戲劇組工作,年齡尚小的小惠和厚祥,則被分配去服務團的少先隊那里參加活動。
從此,阿英同子女都穿上了新四軍軍裝,阿英還發(fā)到了一支小手槍。錢瓔在回憶這段生活時感慨地說:“那時,我們一切都改變了,就連生活方式也變了。”服務團的成員基本上是來自江、浙、滬的知識青年。由于服務團所在地經(jīng)常處于掃蕩和反掃蕩的斗爭環(huán)境,他們就利用戰(zhàn)前抓緊學習排練,為戰(zhàn)士和當?shù)厝罕娮餍麄鞴膭有匝莩觥T趹?zhàn)斗打響后,他們就擔任后勤工作,去打掃戰(zhàn)場。戰(zhàn)后,又抓緊趕排節(jié)目,慰問部隊和群眾。
這時期的阿英不僅為服務團的戲劇組排戲,還親自改編了話劇《小奸細》,并加以排練。為了提高多數(shù)并非科班出身的演出人員的業(yè)務水平,他在簡陋的農(nóng)舍里,開講中國戲劇運動史課,為大家講解表演藝術(shù),滿腔熱情地為大家作輔導。每次演出后,阿英還與農(nóng)民交談,征詢對演出的意見。他對錢瓔說:“從農(nóng)民的反映看,城里演出的戲劇不宜照搬到農(nóng)村,我們要好好研究一下根據(jù)地的戰(zhàn)士和群眾所喜歡和接受的狀況,只有找準了他們可以接受的內(nèi)容和形式,才能真正發(fā)揮戲劇宣傳群眾、鼓舞群眾的作用。”
在阿英的悉心指導和培育下,原來只是演演小戲和活報劇的服務團,后來也能夠演出多幕的大戲了,演出水平大有提高,受到了旅首長和戰(zhàn)士、群眾的好評。
1940年秋,陳毅、粟裕指揮的黃橋自衛(wèi)反擊戰(zhàn),是新四軍打開蘇北局面的一次決定性戰(zhàn)斗。阿英得知一師一旅當時是這次戰(zhàn)役中的主力,便到一旅政治部,請阮英平主任講述這場戰(zhàn)役的經(jīng)過,還搜集了具體資料和查閱有關(guān)檔案。當他了解了這支勁旅是從福建老區(qū)以一桿槍起家,一直發(fā)展到后來改編為新四軍一支勁旅的戰(zhàn)斗歷程后,產(chǎn)生了歌頌弘揚這支部隊英雄業(yè)績的強烈責任感。為了寫好部隊,他不但自己深入到斗爭的最前線,還鼓勵剛到部隊的大兒子錢毅,到前方經(jīng)受考驗。
陳毅與阿英相見恨晚
新四軍代軍長陳毅,很快得到了阿英在一師一旅指導文化工作的消息,托前來軍部開會的葉飛,向阿英傳達要其到軍部工作的指示。這下葉飛只得忍痛割愛了。阿英和四個子女從服務團的所在地泰州地區(qū)出發(fā),歷時45天,到達了新四軍軍部所在地。
在一座新蓋的茅草屋里,陳毅和夫人張茜熱情接待了阿英。性格率直的陳毅,在一番詢問阿英前來的路途情況后,就滔滔不絕地介紹起新四軍文化工作的現(xiàn)狀和問題。他認為:現(xiàn)在蘇北根據(jù)地的文藝作品中,反映新四軍戰(zhàn)斗生活少了,特別是在戲劇方面,更是不夠。為此,他想集中一批文化人,加強部隊的文化工作。希望阿英在軍部工作,把主要精力放在劇本創(chuàng)作上。
對于阿英的到來,陳毅有相見恨晚的感覺。為了與阿英聯(lián)系和交談的方便,他特地交辦將阿英搬到他的臨近處居住。只要是夜晚閑暇,他就信步來到近在咫尺的阿英家里,或帶口信要阿英到他的家里。陳毅非常健談,國際國內(nèi)的大事,從政治、經(jīng)濟到文化藝術(shù),侃侃而談。阿英多數(shù)時間是聆聽,可一涉及文學藝術(shù),他的話語也就多了起來。兩人每次都談得十分投機。陳毅知道阿英有不少藏書,他不僅一一閱讀了阿英在“孤島”時期所寫的一些抗日劇本,而且還借閱了古典文學作品。一次他閱讀了《宋人小說集》《琵琶記》《牡丹亭》,在將書送還給阿英時,還附信寫了他對三本書的評價。
陳毅愛作詩,而當時所作的詩多數(shù)是在反掃蕩作戰(zhàn)中騎馬走筆寫成的,他將這些詩陸續(xù)地拿到阿英處請幫助定稿。阿英很喜歡讀陳毅氣勢磅礴的詩歌,在一年時間里,他就匯集了陳毅的20多首詩,并用毛筆工整地抄錄在毛邊紙上,裝訂成冊,扉頁上題了“阿英手錄”,還蓋上了印章,贈送給陳毅留念。陳毅十分珍愛這冊由阿英精心裝幀的《陳毅詩集》。陳毅辭世近40年了,可這本珍貴的手抄本,如今依然完好地保存在陳毅的子女那里。
1942年秋天,陸續(xù)來到蘇北新四軍軍部的文化人中,還有范長江、賀綠汀、胡考等一批著名文人。陳毅考慮:這些文人可是部隊難得的人才,開展軍隊文化工作離不開他們。于是,他建議在軍部西邊不遠處叫賣飯曹的小村,建立一個文化村,明確由揚帆當“村長”。自此,這些文藝戰(zhàn)士就常在一起,研究、探討部隊的文藝工作。阿英這時很忙碌,軍部的魯迅藝術(shù)工作團、新安旅行團及三師魯迅藝術(shù)工作團,都邀請他去講課。陳毅也常來到這個村里,與文化人暢談,一起下圍棋。
這年的11月,陳毅從團結(jié)鹽阜區(qū)各界人士,做好抗日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工作出發(fā),在鹽阜區(qū)參政會閉幕后,又倡議要阿英、彭康、范長江、王闌西、白桃、薛暮橋、車載及開明士紳楊芷江、計雨亭等作為發(fā)起人,成立了湖海藝文社。阿英起草了六條臨時社約,明確規(guī)定:愿以藝文為抗戰(zhàn)建國服務者,方得為本社社員。后來,阿英在他主編的《新知識》刊物上,特地增辟了《湖海詩文選》欄目。湖海藝文社事實上作為一個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性質(zhì)的文藝人士的組織,在聯(lián)絡團結(jié)各界知識分子,發(fā)揚民族正氣和愛國主義精神,推動抗日戰(zhàn)爭這一偉大事業(yè)中,起到了特殊的作用。
1942年12月初,日偽在鹽阜地區(qū)的又一次大掃蕩即將開始,文化村的文化人屬非戰(zhàn)斗人員,被安排到阜東縣分散隱蔽。阿英被安排到愛國民族資本家創(chuàng)辦的華成鹽業(yè)股份有限公司打“埋伏”。1943年2月中旬,日偽軍兵分五路開展了規(guī)模空前的春季大掃蕩,他們揚言要將新四軍消滅于黃海之濱。阿英在華成公司武裝的掩護下,與公司總經(jīng)理張仲惠一家和公司職工,迅即轉(zhuǎn)移到了30里外的海灘邊緣與敵人周旋。也就在這時,上海的敵偽報紙刊登了“阿英全家遇難”的消息。
1946年年底,解放戰(zhàn)爭進入艱苦的歲月,阿英懷著對老區(qū)人民依戀不舍的感情,離開了他生活了五年多的蘇北老根據(jù)地,踏上了去山東的的征途。
1947年3月,阿英到達了已遭到敵人幾度轟炸的沂水城,19日終于到達了華中分局的所在地于家湖。23日,他急著去坡莊軍部看望非常惦念的陳毅軍長。可是,因陳毅在大諸葛北衛(wèi)生部養(yǎng)病,這天未能見上。誰知,阿英兩天后卻得到了長子錢毅在淮安前線壯烈犧牲的噩耗,使他異常悲痛。27日,阿英與李一氓、張愷帆等又到軍部,終于見到了分別四年多的陳毅軍長。陳毅關(guān)切地詢問了阿英的身體狀況,在談到錢毅犧牲時,陳毅安慰阿英說:“死得很可惜,你要好好地收集錢毅的遺文替他編本集子,好好紀念他。”
上世紀50年代中期,文化部個別領(lǐng)導硬說阿英歷史上有問題,對他采取了隔離審查。文聯(lián)有位領(lǐng)導出于正義,親自找到了對阿英深有了解的陳毅副總理進行調(diào)查。陳毅一聽大為震怒,當場提筆寫了材料,證明阿英歷史上沒有問題。就在這份材料的結(jié)論處,陳毅特別加了三個很大的驚嘆號。自此,文化部的有關(guān)領(lǐng)導也就不敢再對阿英擅自審查了。1957年的冬天,阿英患了腦血腫在北京醫(yī)院動了大手術(shù),周恩來得悉后,在百忙之中到醫(yī)院看望阿英,叮囑大夫要給阿英進行精心治療。
根據(jù)張愛萍建議創(chuàng)作話劇《李闖王》
1944年,世界反法西斯戰(zhàn)爭出現(xiàn)了重大轉(zhuǎn)機,這年3月,郭沫若眼見抗戰(zhàn)即將迎來勝利,他以歷史學家的遠見,考慮了勝利后防止驕傲和腐敗的問題,以史為鑒寫了《甲申三百年祭》一文,發(fā)表在重慶《新華日報》上。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非常重視郭沫若的這篇文章,不僅在《解放日報》和敵后各根據(jù)地黨報上予以轉(zhuǎn)載,而且將它作為干部整風學習的參考文件。
根據(jù)黨中央的部署,蘇北抗日根據(jù)地的黨政軍領(lǐng)導干部,很快掀起了學習《甲申三百年祭》的熱潮。這時,三師副師長兼八旅旅長張愛萍對阿英說,如能將李自成的歷史寫成一個劇本演出,這對干部戰(zhàn)士進入城市前,將是很好的思想教育教材。阿英聽后盡管感到當時的戰(zhàn)爭環(huán)境中,創(chuàng)作劇本困難很大,但一想到寫這樣的歷史劇意義非同尋常,難度再大也應當克服。于是,他憑著自己腦海里積累的資料,加上收集到一些,先編寫了一個《李自成年表》,隨后很快擬好了劇本的分幕和分場提綱,爾后大約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完成了初稿,接著又作了反復修改。3月初,劇本一定稿,就開始幫助八旅文工隊一邊排練,一邊再作修改。
經(jīng)過緊張排練,大型歷史劇《李闖王》就要演出了。但是,沒有室內(nèi)舞臺,沒有古代服裝,燈光、道具、布景也遇到了困難。經(jīng)過阿英和文工隊全體同志齊心協(xié)力,因陋就簡,都被一一解決了。5月6日晚上9時,在阜寧益林鎮(zhèn)郊外廣場搭的土臺上,五幕歷史劇《李闖王》一直演到了深夜兩點才結(jié)束,觀眾有2000余人。
這天,阿英拿了小板凳,就坐在觀眾中間,邊看邊注意聽取群眾的反映。戲一散場,他顧不上休息,就伏在豆油燈下連夜修改劇本。
三師師長黃克誠在演出的第二天寫信給阿英。信中說:“這個戲演給干部看,是會有很好影響的。”《李闖王》在鹽阜地區(qū)巡回演出了30多場,還到蘇中東臺等地,為一師的指戰(zhàn)員演出。1946年后,《李闖王》在東北地區(qū)演出了60多場。新中國成立前后,這個戲在華東、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昆明等地演出達400多場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