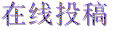很長一段時間里,我對母親的感覺是模糊的。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孩童時的一個場景——我啃著饅頭去上學,走到省軍區大院門口,看到一個蓬頭垢面,手上腳上裂著許多口子,身上裹著一個破麻袋的男人,在墻角啃一塊紅色的磚頭。我還沒有反應過來是怎么一回事,那人沖到我面前,變魔術一般,我的手上麻了一下,饅頭掉在地上。那人撿起我掉在地上吃了一半的饅頭,一口吞了進去。我看見他的喉嚨那里有一個大包,他的眼睛直往上翻,他用布滿血絲的手使勁從上向下擼脖子,終于他的眼睛又翻了回來,我嚇得哭出聲來。
那年我6歲,上小學一年級。
晚上見到父母后,我把這事告訴了媽媽,說那個站崗的解放軍叔叔,看著那個人把我手中的饅頭拍到地上也不管,站在那兒動也不動,像個木頭人。媽媽爸爸交換著一種我從未見過的眼神,媽媽那雙美麗善良的大眼睛有點濕潤,她立即轉過身去。爸爸生氣地說:“你少吃一個饅頭不會死,那個人不吃說不定就死了。”我不知道爸爸為什么會發這么大的脾氣?我說錯什么還是做錯什么了嗎?我很委屈,眼淚怎么也止不住地流下來。媽媽把我拉到客廳說:“現在鬧自然災害,很多人都吃不飽飯,部隊還好,那半個饅頭如果能救活一個人你是不是做了件好事?那位解放軍叔叔沒有錯。”這是母親第一次這么認真和我談話。
我記事的時候母親已經從部隊轉業了,在一個公社任黨委書記。那時城市也按公社劃分,其實就是現在的某某區。我每天清晨醒來,媽媽已經上班去了,有時很晚媽媽才回來。她的臉上永遠都掛著燦爛的笑容,那時候的人精神面貌幾乎都如此。媽媽總是穿著那身洗得發白的舊軍裝,來去匆匆。母親很少有時間坐下來和我們姐妹說些什么,她似乎永遠有忙不完的工作和家務。每個月發工資,媽媽第一件事就是買上一斤糖,兩條肥皂,兩條煙,再放上15元錢,托人捎給外婆外公。
有一次,我小學的班主任對我說:“聽說你母親是新四軍的,我想請她來學校為我們做一次打日本鬼子的報告。”我對媽媽說了此事,媽媽嚴肅地說:“那么多戰友犧牲了,他們才有資格做報告,我們活著的人除了努力工作,沒有它想。”
我們兄弟姐妹9個人,父母還要撫養我一個沒有工作的姨娘,按照那時的級別劃分,父親也算個高級干部了,可生活過得緊巴巴的。母親心靈手巧,會把一些舊衣服翻新,把大衣服改小,改得很漂亮,給我們姐妹穿,她總是想盡辦法把我們姐妹打扮得很得體。以至于一直到如今的初中同學會,還有許多同學說,肖家公主個個是美女,竟然把這話發到了微信群里。
母親從來也沒和我說過她戰爭年代的事,她也從沒有和我說過什么革命大道理。高中的時候,我入團了(那時候在高中能入團的人很少),我很得意地告訴媽媽:“我15歲就入團了。”沒想到媽媽說了句:”不要驕傲,媽媽15歲就入黨了。”我的臉一下子紅到脖子根,如果不是我入團這事,也許我一輩子也不知道媽媽15歲就入黨了。
我對母親知道的甚少,有一次我對她耳垂上的耳洞發生了興趣,我說:“你們這些革命者還戴耳環啊?媽媽說:“參加革命的時候,走得勿忙,什么也沒帶,從小外婆給的金耳環,早就當黨費交了。”
母親在我眼里一直就是一個善良美麗的媽媽,盡管家里隨處可見她穿軍裝的照片,但我從不知她在軍中的職務,也不知道她到底是哪個部隊的。直到陳毅去世那年,我見父母哭得兩眼通紅,方才如夢初醒,知道他們曾經是新四軍。
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父母當著我這個孩子的面痛哭,著實讓我嚇了一跳。我小心翼翼地問母親:“你們怎么會對陳老總有這么深的感情?”
媽媽說:“你爸爸外語好,參加革命前是美國教會學校畢業的,筆桿子硬。解放后,陳老總想調他去外交部,他舍不得這身軍裝,就推薦了另外兩位同志去。現在都是駐外的大使,就是你經常在報紙上看到的那兩位。”
如果不是這次親眼所見親耳所聞,我永遠都不會知道他們和陳老總還有這么一段淵源。
我參軍的時候,媽媽對我說:“少說多做,別人的好處要背后說,缺點要當面說。”我說:“為什么?”媽媽說:“缺點背后說人家沒法改啊,好話當面說不是恭維人嗎?君子不做這樣的事。”
媽媽如果九泉之下有知,一段時間世風竟是當面說好話,背后下絆子,不知作何感想?
我并不知道母親年輕時的那些往事,平時看到的總是她忙碌的身影,我覺得她們那一代人早就把生命交給信仰了。
上個世紀80年代初,我在南京軍區藥訓班學習,地點在浙江臨安。一天,突然有領導找到我說:“剛才接到電話要你去無錫,車票已給你買好,現在就走。”領導一臉世界末日的表情,我預感不測,眼睛濕了。領導忙說:“別急別急,電話并沒有說你母親有事,只說在搶救。”藥訓班的領導和學員簇擁我上了長途汽車。我帶著一絲僥幸心理,到了無錫101醫院門診部。被告知:母親車禍,當場死亡。聽此言,我立即昏死過去,醫生護士手忙腳亂把我搶救過來。
后來的追悼會是我有生以來出席的最為隆重的追悼會,有100多家單位發來了唁電,李德生和夫人也發了唁電。市委大禮堂擠滿了人,很多人只能站在禮堂外的空地上,最后連禮堂外的空地也站滿了人,人們只能站在市委大門外的街道上……追悼會上驚天地動鬼神的哭聲至今還常常把我從睡夢中驚醒。最令我們姐妹感動的是,她的部下連夜給母親趕制了一件呢子大衣,哭著說:“你母親太樸素了,連一件像樣的呢子大衣都沒有……”
母親的戰友和同事哭得比我們孩子還傷心,堅持不讓我們孩子守靈,她的戰友和同事集體為我母親守靈7天。母親的一位單位同事在我耳邊說,我以后或許再也碰不到這么好的領導了。
追悼會后,不斷有工人農民到我家來還錢,說是母親借給她們的,數量不多,也就幾元,幾十元的。父親知道,那是母親在基層搞調查研究時幫助有困難的群眾,并不是借給她們。就說,她不是借給你們,是幫助你們的,別還了。
正是追悼會那一天確立了我的三觀,也是在那一天,我第一次知道母親在那些普通群眾心中的份量。
受《鐵軍》雜志編輯之約,要我寫一篇有關母親在新四軍的文章。我真是萬分為難,因為母親幾乎從未和我講過她在新四軍的故事,只好請教我的幾位姐姐。幾位姐姐都說:“平時,媽媽從不和我們說她的革命經歷。”只有仍在軍中的三姐說:“我可以提供一個細節:有一次我的一個戰友結婚,她母親給她一個金戒指。我回家問媽媽:我那個戰友的母親和你背景差不多,她有好幾個金戒指,每個孩子都有,大小不一,你打仗的時候就沒有看到?”
媽媽說:“打鬼子炮樓時,何止金戒指?金項鏈,金手鐲多的是。”三姐問“: 你就沒拿點?”媽媽說“: 誰拿那個,明天活不活還不知道呢,都搶武器。”三姐還說“: 我以為媽媽要說什么革命大道理,或者三大紀律,八項注意,沒想到她說的是這個,可見那時的新四軍戰士隨時準備犧牲。”
有這么一支軍隊,有這么一群人,中國革命怎么會不成功?!
母親仙逝已經38年了,她的墓地已經演變成一個風景旅游區。有一次掃墓我竟然找不到準確的地點,找到墓區管理辦公室,那位同志很熱情地說“: 是烈士墓吧?”我說“: 是。”陪我去的妹妹說“: 不是。”那位同志說“: 是革命良母李林之墓吧?”我說“: 是的。”那位同志轉過身對我妹妹說“: 你怎么說不是呢?我們這兒就一個烈士墓。”在我妹妹心中只有犧牲在戰場上才叫烈士。那位同志又說“: 在我們心中,打過日本鬼子的都是英雄,都是好樣的,死后都是烈士。”
很多年過去了,每當我看到有關新四軍的電視劇,看到熒屏上那些美麗清純的新四軍的女兵,我就會熱淚滂沱。女兒總是很驚詫地問:你為什么會哭?我會在心里說:因為我見到了你的外婆……
(肖靜,中國作家協會會員。作品多次獲獎,報告文學《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》獲改革開放30年征文金獎,入選普通高中課程標。長篇報告文學《天降大任——吳棟材與五個村莊的命運》獲江蘇省第四屆紫金山文學獎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