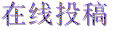隆冬的傍晚,北邊的云團(tuán)層層疊疊向南涌來,稍頃,鵝毛大雪漫天飛舞。新四軍第四師政治部直屬文藝隊(duì)?wèi)?zhàn)士雷詩穎倚靠在門框上,雙手纏繞著垂掛胸前的長辮,目光望向蒼茫雪野,心思卻拴在了百米外的那一頭。
這是1943年歲末。盡管這年的頭場雪才下了兩個(gè)多時(shí)辰,但由于伴著氣溫陡降,大地已積下厚厚的雪毯。雷詩穎揣著即興寫就的《雪夜》詩,踮著腳尖輕步跑向百米外的茅屋,那是文藝隊(duì)指導(dǎo)員凌云志的宿舍。然而,就在走近茅屋時(shí),雷詩穎猛然愣住了,茅屋里跳動(dòng)著的燭光,襯映出一幅剪影,顯然是兩個(gè)人相依在一起。剎那間,雷詩穎心頭突生一種眩暈感,身體軟軟地靠在老槐樹上。她想立刻轉(zhuǎn)身離去,但透過窗欞的光亮投射在雪地上,恰似編織出一張碩大的網(wǎng),把她緊緊罩在其中無法抽身。她走近些,定神看去,只見凌云志盤腿端坐床邊,一個(gè)穿軍服的姑娘溫順而無力地倚靠著他,他左手端著陶碗,神情專注地往姑娘嘴里喂著什么。
那一刻,縱是千萬般的柔情似水,雷詩穎也無法抑制心底的劇痛,一咬牙掏出墨香尚存的《雪夜》詩箋,奮力撕碎扔向天空。此刻姑娘的一顆芳心,亦如飛揚(yáng)的詩箋碎也碎也。
戰(zhàn)事頻仍的年代,一切都顯得匆忙與急促。對于被邊緣到幾乎出局的情感問題,更是無暇深究。翌日清晨,雪霽天晴,雷詩穎便徑直找到政治部領(lǐng)導(dǎo),毅然決然地要求調(diào)到戰(zhàn)地學(xué)校當(dāng)教員,并當(dāng)即得到批準(zhǔn)被送往學(xué)校駐地。
這天雷詩穎所持的介紹信,時(shí)間落在1943年12月16日。這一年,雷詩穎20歲。
孰不知,這個(gè)雪夜一瞥帶來的陰差陽錯(cuò),竟導(dǎo)致了一雙戰(zhàn)地戀人的陰陽兩隔。20世紀(jì)90年代的一天,一位工于玉石雕刻的詩人探訪病中的雷詩穎。交談間,偶然瞥見書柜正中央擺放的一朵奇異紙花,竟不由自主地撂下談興正濃的話題,徑直走到書柜前細(xì)細(xì)端詳。再三追問下,雷詩穎才向這位她信賴的詩友說起詩箋花,以及蘊(yùn)藏其中的那段戰(zhàn)爭歲月的凄美戀情。
那個(gè)雪后晴朗的冬日,雷詩穎被送往駐臨渙古鎮(zhèn)文昌宮的戰(zhàn)地學(xué)校,擔(dān)任文學(xué)和音樂教師。她上的第一堂文學(xué)課是《詩經(jīng)》,教的第一首歌是《義勇軍進(jìn)行曲》。她跟同學(xué)們講歷史璀璨的祖國、戰(zhàn)火蹂躪的家鄉(xiāng),拉著帶到延安又輾轉(zhuǎn)淮北的小提琴教唱《松花江上》。當(dāng)雄渾高亢抑或低回哀婉的曲調(diào)激蕩胸間時(shí),她的眼中噙滿了晶瑩的淚水,同學(xué)們明凈的雙眸也閃動(dòng)著淚光,但回蕩在教室里的歌聲卻愈加充滿力量。
文昌宮,數(shù)年后一度成為淮海戰(zhàn)役的指揮中樞,只是當(dāng)時(shí)的雷詩穎并沒有想到。置身于此,與其說是尋找一隅情感逃避的凈土,不如說是新辟了一方釋放激情的陣地。雷詩穎把淤積心底的感情傾注給了戰(zhàn)地學(xué)校,傾注給了于戰(zhàn)火紛飛中稚嫩的臉龐仍寫滿憧憬的學(xué)生們。她不知道,就在她前往文昌宮的當(dāng)天,百思不解、傷心至極的凌云志也遞交報(bào)告,調(diào)往特務(wù)營擔(dān)任二連指導(dǎo)員。
戰(zhàn)爭,以其慣有的殘酷,制造著無以數(shù)計(jì)的悲歡離合。雷詩穎與凌云志的情感糾葛最終在一年后畫上了逗號(hào)。那個(gè)冬日黃昏,雷詩穎教授文學(xué)課,在布置完作業(yè)后,她獨(dú)自佇立在窗邊。教室很靜謐,唯余寫字的“沙沙”聲。窗外,夕陽西下,落日的余暉在蒼穹邊緣抹上了一片腥紅。驀然,一種感應(yīng)流星般滑過腦際:今天是她與凌云志分手的周年日。意念來得突然卻很具沖擊力,雷詩穎不禁打了個(gè)寒戰(zhàn),下意識(shí)地交叉雙手抱緊了肩胛。就在這當(dāng)口,鎮(zhèn)東頭遽然傳來密集的槍聲和劇烈的爆炸聲。雷詩穎立即組織同學(xué)們轉(zhuǎn)移隱蔽。那一刻,她的心底突然有了一種異樣的忐忑,待到槍聲稍顯稀疏,便不顧一切地向城外奔去。在城墻根,她的生命遭遇了錐心的痛楚。就是這個(gè)冬日,凌云志率領(lǐng)一排戰(zhàn)士追擊一支行動(dòng)詭秘的日偽小分隊(duì),在探明敵人襲擾臨渙古鎮(zhèn)企圖的瞬間,凌云志果斷地命令部隊(duì)出擊,兩軍在古城墻下猝然交火,戰(zhàn)斗打得異常艱苦。雷詩穎趕到時(shí)戰(zhàn)斗剛結(jié)束,土坡上橫七豎八地躺著十幾具日偽軍的尸體,而凌云志與另七個(gè)犧牲的戰(zhàn)友則并排靜靜地躺在墻根下,一顆罪惡的子彈擊中了他的左胸口。
那個(gè)瞬間,雷詩穎大腦一片空白,淤塞心頭的曾經(jīng)的怨忿瞬間蹤跡全無。跪在烈士遺體旁,雷詩穎悲痛萬分地凝視著曾經(jīng)的戀人。凌云志兩道劍眉緊擰著,右下唇被牙齒咬破滲淌的鮮血已成暗紅色,直至犧牲倒地仍保持著激憤殺敵的神勇。中彈的左胸上衣口袋已被撕裂,露出一疊淺黃的紙頁。雷詩穎陡然感到心頭突遭彈擊般地劇烈一顫,那正是她心血與情感凝結(jié)成的信物啊!
詩人斂聲屏息地聽著敘述,他突然間明白了至情至性的雷詩穎終身未嫁的緣由,亦讀懂了她的作品緣何有著那么濃郁的蒼涼感和空靈感。一個(gè)穿越戰(zhàn)火硝煙的知識(shí)女性,一個(gè)敢愛敢恨且情專意篤的客家才女,在經(jīng)歷了那樣一番天崩地裂的情感創(chuàng)傷后,擺脫世俗的羈絆與情感的束縛已屬必然。詩人再次起身走到詩箋花前。
詩箋花緣于子彈洞穿的強(qiáng)烈沖力而窩成喇叭狀,彈孔周邊的箋頁被鮮血粘連,而外沿則撕裂卷曲,整疊詩箋如花綻放。烈士鮮血的浸染,更令詩箋花那份攝人心魄的紅由內(nèi)向外、由深至淺,自然無痕地層層洇漫,釋放著穿越時(shí)光的厚重信息:那不再是一個(gè)平凡的紙質(zhì)物件,而是一個(gè)凝駐忠烈英靈、超越自然形態(tài)的生命載體。
詩人再次被震撼了,佇立詩箋花前良久無語,半晌,猛一擊掌,未告別便匆匆離去。兩天后,詩人再次登門,送上了一件藝術(shù)精品。他用珍藏多年的一塊極品雞血石,雕刻出一枚玉質(zhì)詩箋花,那溫潤剔透與高貴雅潔,令人不忍觸摸。為兩枚詩箋花配制的青檀木底座,抽象的心狀座托,精巧逼真地勾勒出花萼的蔥翠,磚形座基四周環(huán)繞著長城立體浮雕,靈動(dòng)傳神地詮釋著烈士的忠貞赤誠。詩人說,是戰(zhàn)地絕戀的凄美與彈穿詩箋的慘烈,讓寶石找到了無可替代的歸宿,擁有了無與倫比的生命內(nèi)蘊(yùn)!
如今,兩枚詩箋花被收藏在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。參觀的人們每每經(jīng)過展柜,都要駐足,凝視良久。
我沒有追根溯源地去研讀雷詩穎的詩文,以她的超凡閱歷和聰穎,于文壇上綻放異彩自然毋庸置疑。只是那個(gè)雪夜邂逅目睹的一幕,又有怎樣的解釋能讓內(nèi)心遭受創(chuàng)傷的巾幗英杰得以釋懷?我查閱了很多史料,最終是詩人的一篇補(bǔ)記給了我答案。
1942年的歲末,雷詩穎,這個(gè)出自湘西書香門第的北大才女,在看了手寫傳抄的毛澤東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(huì)上的講話》后,心潮澎湃,激情難抑,只身輾轉(zhuǎn)千里到達(dá)延安,經(jīng)過半年培訓(xùn),被分配到新四軍第四師文藝隊(duì)擔(dān)任歌曲創(chuàng)作員。僅三個(gè)月時(shí)間,她創(chuàng)作的十多首歌詞被譜曲后,春風(fēng)沐雨般唱響了長江南北的新四軍部隊(duì)。而她與指導(dǎo)員凌云志之間的十多首情詩來往,則締結(jié)出一份曠世情緣。
時(shí)光回溯到1944年12月16日的那個(gè)黃昏。殘陽如血,寒風(fēng)疾速掠過,在滔滔澮河與逶迤城墻間凄厲地呼叫泣訴。雷詩穎用顫抖的雙手解開烈士左胸口的衣兜,小心翼翼拈出的是她寫給他的16首詩的詩箋。那一刻,雷詩穎心痛的情狀無以言表。16首,16日,她與凌云志相戀的情感之旅,她魂?duì)繅艨M的戀人的生命足音,俱于這組數(shù)字重疊處戛然止步。她聲淚俱下地對他說,早知上天有這樣的安排,她寧愿廢寢忘食寫上千行萬首,用自己的真情蔭佑他生命的延續(xù)。然而,一切都已無可挽回,罪惡的子彈穿過那摞折疊的詩箋,無情地嵌入了英雄的軀體。
抗戰(zhàn)勝利后,雷詩穎被調(diào)入華野文藝團(tuán),踏上了淮海戰(zhàn)役、渡江戰(zhàn)役和解放大西南的漫漫征程。盡管軍旅生涯輾轉(zhuǎn)顛沛、險(xiǎn)厄相隨,但那簇鮮血凝成花形的詩箋始終被完好地保存著。新中國建立后,雷詩穎專門請工匠制作了一個(gè)精美的水晶匣,抽去氧氣,讓詩箋花置于真空狀態(tài)下保存。
1954年的那個(gè)冬日,雷詩穎專程回到淮北,踏上臨渙東那片故土,拜祭犧牲10周年的英雄戀人。在烈士墳冢前,雷詩穎與十多年前燭光依稀中閃現(xiàn)的那個(gè)女子不期而遇。經(jīng)介紹,得知她叫凌云芳,是凌云志的胞妹。那個(gè)冬日,新四軍四師野戰(zhàn)醫(yī)院遭日寇空襲,傷員被星夜分送鄰近部隊(duì)養(yǎng)傷,負(fù)傷的衛(wèi)生兵凌云芳就此住進(jìn)了哥哥凌云志的茅屋。塵封11年的那一幕終于揭去面紗,那一刻,強(qiáng)烈自責(zé)與劇烈痛憾,直如驚雷貫頂,終令矜持自負(fù)、寧折不彎的湘西才女,無法自持地暈倒在凌云芳的懷里。
時(shí)光有時(shí)就像冰雪,會(huì)把曾經(jīng)發(fā)生的一切掩埋湮滅,但詩箋花留給世間的真情與清香,溫暖雋永。